试图洞彻哲学的深度,是我毕生之所爱。
——理查德·瓦格纳《我的一生》

按照这一整体艺术的至高理想,瓦格纳对传统歌剧作出了重大革新,首创了“音乐戏剧”(Music Drama,以下简称“乐剧”)这一概念。传统歌剧以歌曲为主体,而在瓦格纳的“乐剧”中,管弦乐笼罩了整部歌剧的所有环节,其它的复调线条如声乐——尤其是在传统歌剧中占主导地位的咏叹调降到了次要地位。于是,旋律与和声这两个音乐中的最基本要素在歌剧中的作用此消彼长。瓦格纳认为就戏剧而言,音乐是引起这种效果的决定性的艺术,而戏剧中的其它艺术,如诗、建筑、绘画、雕塑,都是为了强化这种效果。对此,他曾这样描述:“它把真实的那僵硬的、呆滞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融化成为流动柔软地顺从的、感受印象的、精气般的平面,它那不可测量的底层就是感情的海洋本身。”以这种效果为目的,以音乐艺术为中心,诸种艺术便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艺术”。
客观而言,瓦格纳“整体艺术”观照下的乐剧创作理念引领了西方音乐史的发展潮流。19世纪上半叶,德国人普遍认为德语不够雅致,宫廷内外盛行意大利与法国的歌剧,偏重音乐技巧上的华丽而忽视戏剧的内容,瓦格纳的这一创举几乎改变了音乐史对于传统歌剧的认知,甚至影响了20世纪电影和电影配乐的发展。一方面,他提出的“主导动机”(leitmotif)概念将戏剧张力、场景、人物以及抽象的情感和哲学内涵同音乐具象连接,对后世无数音乐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歌剧史乃至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创新。另一方面,他对过去只在前奏曲(Prelude)或序曲(Overture)中出现的管弦乐团的革新极大地增强了管弦乐的表现力,使其成为统一全剧的支柱。从此,瓦格纳歌剧成为西方歌剧中的一个单独类型,连同拜罗伊特这个圣地,深深地刻在了全世界瓦格纳乐迷的心中。
然而,就主观感受而言,对于瓦格纳歌剧的评价呈现出非常两极化的倾向——热爱者顶礼膜拜,反感者则视如敝屣。海德格尔曾说,瓦格纳追求的是“音乐艺术那样的支配力和情感的纯粹状态的支配力——感官的喧嚣和迷狂、可怕的挛缩、令人如痴如醉的忧伤、消融于如海一般的和谐、投入疯狂之中、在救赎般的情感中四分五裂。”听听他那辉煌而冗长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他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我们就能明白,瓦格纳的“整体艺术”追求的是统治一切的纯然感受,那里有最高度的热情,有不可遏制的官能欲望,有最阴森的悲观主义,这一切都最终体现为对观众的感受的支配——尤其是突出和声而弱化旋律的做法,更是让听众难以记住其中的歌唱段落。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瓦格纳音乐中唯一耳熟能详的或许只有那首《婚礼进行曲》了。

笔者收藏的部分瓦格纳首版唱片最终,在尼采的攻击声中,在托尔斯泰的责骂声中,在希特勒的痴迷声中,瓦格纳的艺术乌托邦坍塌了。他的全部创作代表着音乐的梦想与美学的梦想,如果能够以艺术的方式进行一场革命,来对抗现代性的恶果,并塑造出完整的人,如果这些都是可能的,这无疑将使艺术和美学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虽然瓦格纳没有成功,但他却指出了一条新路,正如海德格尔曾引述的尼采的一段话:“他在每一个方面唤醒了新的价值判断,新的欲望,新的希望……谁没有从瓦格纳那儿学到些什么呢?”瓦格纳与叔本华
从费尔巴哈到尼采,哲学情结浓厚的瓦格纳一生中受到诸多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对其歌剧创作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叔本华。在《瓦格纳》这本传记中,汉斯·马耶尔(Hans Mayer)在“引路人叔本华”一章中写道:“瓦格纳这个失败了的革命家,现在也像他的许多同路人一样,在自己的道路上找到了叔本华的思想王国。”事实上,这样说并不准确,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哲学头脑的音乐家之一,瓦格纳在阅读叔本华之前已经写下了《艺术与革命》(1849)、《未来的艺术品》(1850)、《歌剧与戏剧》(1850-1851)等多篇重要论文,一种他所独创的“乐剧”观念正在酝酿——音乐不再是戏剧的陪衬,而是戏剧的对手,甚至成为主角。因此,毋宁说叔本华哲学和瓦格纳音乐幸运地相互找到了对方。1854年秋天,在一封写给李斯特的信中,瓦格纳写下了一段真实而伟大的自白:
我现在只在研究一个人,用文学的语言来说,他像上天馈赠的一般出现在我的孤独里。这就是阿图尔·叔本华,他是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在他面前,所有的黑格尔们都是些江湖骗子!他的主要思想,即对生命意志的最终否定,具有非常严肃的、但又唯一具有拯救的意义。……正是这位哲学家唤醒我,让我明白了这种思想。
1857年仲夏,瓦格纳作出了一个令人愕然的决定,他突然完全中止了史诗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并在给李斯特的信中写道:“我把年轻的齐格弗里德领进了可爱、孤寂的森林世界,让他呆在一颗菩提树下,我从内心深处流着热泪向他告别了。”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持续的来自叔本华思想的震颤中,瓦格纳毅然离开了《指环》的世界,转而投身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创作之中,瓦格纳以其勃勃的野心,企图以一部划时代的音乐戏剧来诠释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思想,诠释其“音乐作为最高艺术”的美学思想。事实证明,这部乐剧被公认为西方歌剧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作品。
此剧取材于古代传说和中世纪文学,但瓦格纳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删减和改动。武士特里斯坦爱上国王之(未婚)妻伊索尔德,这份有悖人世伦理规范的情爱因迷药的推波助澜而愈加不可遏制,两人置警告和危险于不顾,忘情于海誓山盟之中。在艰难的困惑和挣扎后,两人最终平静而欣喜地接受死亡,以此才得以解脱“意志”的摆布并达至永恒的涅槃。贯穿该剧的主线是一个具备典型“叔本华式”色彩的核心意念,即无法抗拒的爱欲是生命中的最高实质,它全盘掌控,支配一切,卷入其中的凡人只能听任这个无所不在的“意志”,最终通过献出生命来获得精神救赎。
瓦格纳与尼采
作为西方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关键人物,尼采以“上帝死了”的预言引爆了西方古典思想的信仰世界。极为相似的是,作为西方古典音乐向现代音乐过渡的里程碑式音乐家,瓦格纳则以“整体艺术”、“主导动机”、“特里斯坦和弦”(半音化和声)等一系列重大创新,同样引爆了西方传统音乐的审美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两位西方文化史上的巨人有过一段漫长而耐人寻味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了瓦格纳不只是一位音乐家,更是具备深厚哲学和美学修养的哲人(甚至不少人将瓦格纳视为美学家),而尼采也不只是哲学家和诗人,还是一位痴迷音乐的业余作曲家。于是,这段著名的公案被公认为是解读瓦格纳和尼采乃至19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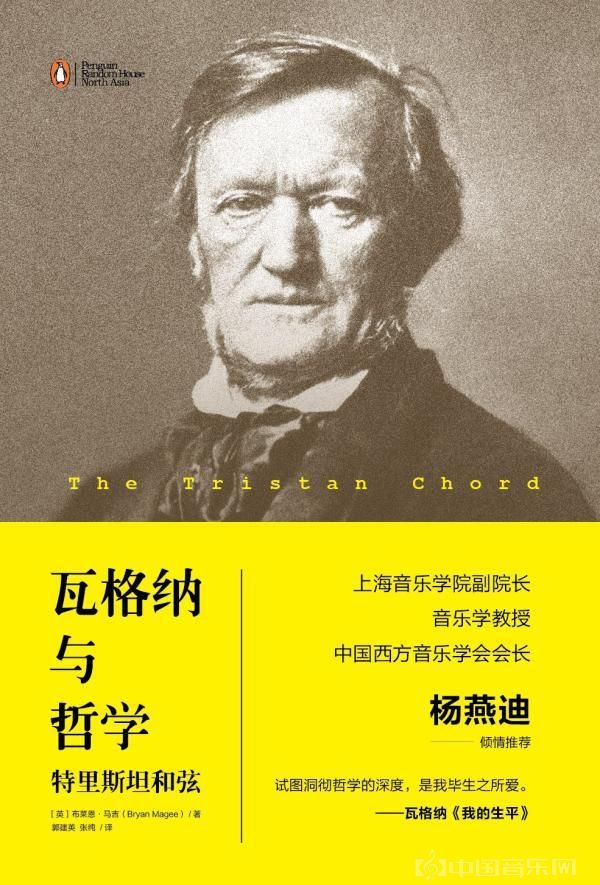
由于尼采对瓦格纳神交已久,而瓦格纳也对这位热爱音乐和哲学的大学生青睐有加,尤其当两人谈到彼此共同的精神偶像叔本华时,可谓一见如故。就这样,瓦格纳很快写信邀请尼采去他特里布森的家中做客。奇妙的是,就在离开的前夜,他的儿子齐格弗里德出生了。“照我的妻子的看法,您是生命带给我的唯一的收获”,瓦格纳不吝赞词,尼采完全被他们接受为家庭成员,甚至成为了“瓦格纳和齐格弗里德之间的纽带”。正是在瓦格纳及其艺术精神的激励下,尼采于1871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受到古典语文学界的无情围剿,但瓦格纳却写了一封致尼采的公开信来为他辩护。直到1872年瓦格纳移居至拜罗伊特前,尼采拜访瓦格纳的次数高达二十多次。在这一两年间,这段纯粹的忘年友情达到了一个高潮。
然而,到了1874年两人的关系却呈现出急转直下的态势。尼采越来越多地看到自己与瓦格纳的不和谐,他在笔记中描述瓦格纳“具有双重性格,难以相处,傲慢自大;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缺乏节制与适度;他把一切都做到极致极限、穷其力量,滥用其情感……”是年春天,尼采在巴塞尔观看了勃拉姆斯《凯旋之歌》的演出,随即买下了这部作品的总谱,并在8月将之带到了拜罗伊特,竟当着瓦格纳的面弹奏了这部作品。要知道,作为德国音乐中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立的两极,勃拉姆斯是瓦格纳一生的最大对手。因此,当瓦格纳看到此情此景时立刻勃然大怒,他觉得这是尼采对他的挑衅,似乎在说:“瞧瞧!你的对手也能创作出很有价值的音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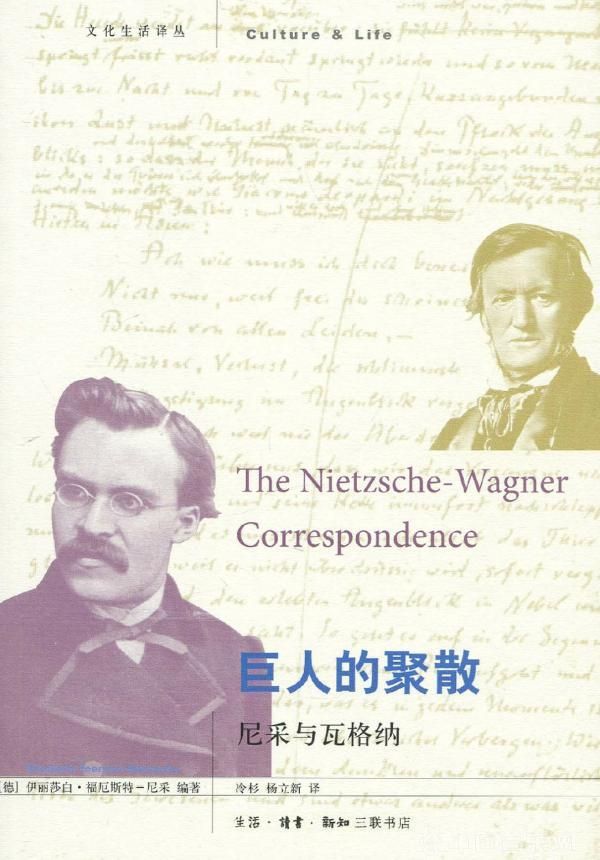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