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杨青先后创作了各类作品数十部,既有民族器乐合奏、重奏、协奏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大合唱,又有影视音乐、舞蹈与舞剧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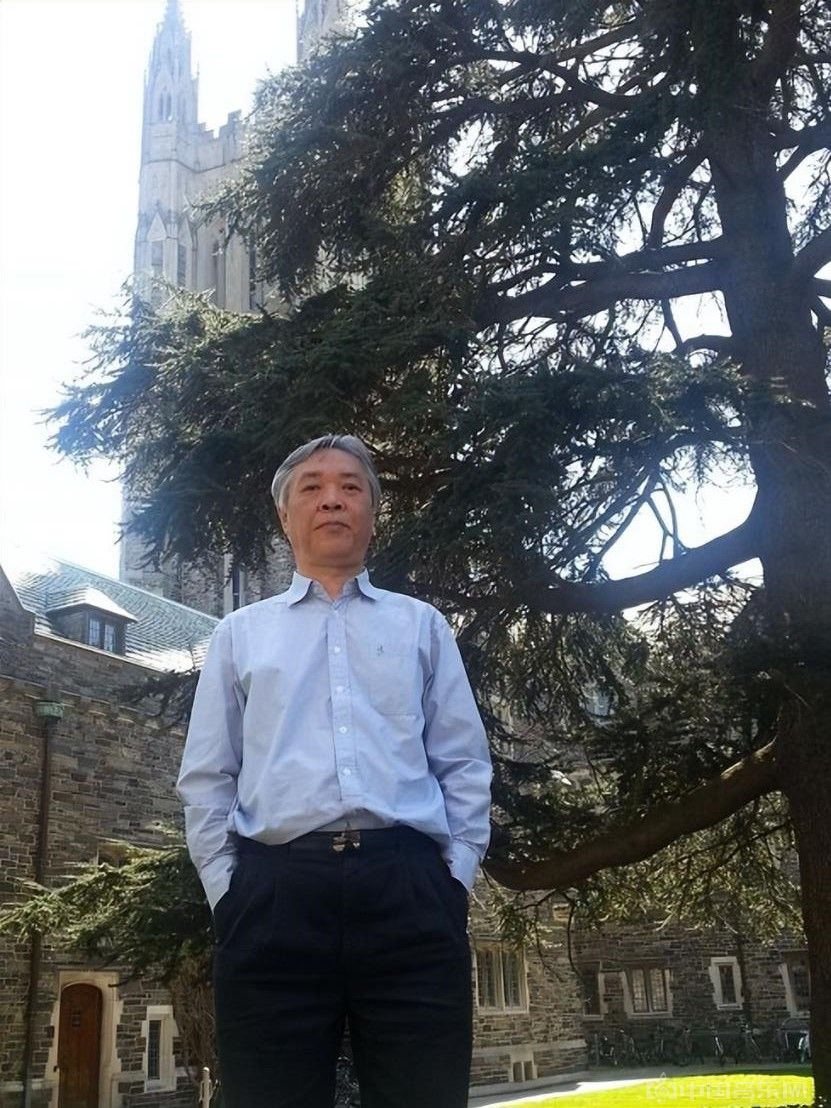
作曲家杨青
杨青,著名作曲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现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音乐创作》编辑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名作曲家,杨青先后创作了各类作品数十部,既有民族器乐合奏、重奏、协奏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大合唱,又有影视音乐、舞蹈与舞剧音乐,例如:《苍》、《觅》、《竹影》、《伊人》、《水中的舞蹈》、《兰花花》、《北京述说》等。
您创作了很多的知名作品,影响都非常大,那么您在作曲方面取得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杨青:我觉得概括说来有五个方面:第一,要热爱作曲,热爱创作。如果不够热爱,很难有创作的激情。其实很多作曲者,并不是十分热爱作曲,他们只是在痛苦
第二,要构建自己独特的语言。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作曲家数不胜数,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有自己个性的语言。如果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个性,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个性语言的建立,一方面来源于作曲家对自己出生的地方,以及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建立的一种血脉上的联系。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方言、音乐、戏曲、歌舞、甚至地方的饮食,都会使他慢慢形成对作曲语言的独特追求,但这也是要建立在热爱作曲的基础上。当作曲家对这里的山水风景和风土人情抱有深深的热爱,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才能建立自己独到的语言,他才能有意识
另一方面,在作曲家创作的笔触上,虽然看起来都是五线谱,
第三,要有扎实的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没有经过千百次锤炼,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写作乐队,需要作曲家了解不同乐器之美,知晓每一件乐器的特性,发音的特点,以及不同乐器结合在一起能产生何种的效果,这些都要非常认真的学习和体会。现在的音乐学院中,一般作曲系学生要求五年毕业,其他专业则不一样,只需四年。音乐学院中,作曲专业和指挥专业都要求五年毕业。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两个专业确实需要学习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与文献资料。
第四,要有广阔的视野。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作曲家不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匠人,他应该
第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情感。其实情感说起来是很模糊、很抽象的。什么叫有情感?就是创作出的音乐是否动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技术,只有个性,只有很高的知识素养,不见得能写出优秀的曲目。
音乐是最淳朴,最能直击人心,引起共鸣的一种艺术。听到好的音乐,人会不由自主
虽然作曲看上去只是在运用一些抽象的符号,但是它的落点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对所有人都带有的深深情感。这种情感的出发点一定是善良,凡是伟大的作曲家都对人类怀有一颗善良的心。这种大爱一定会反应到创作当中,反应到每一个音符上,他们对自然,对生命都有着深层的尊重和敬畏。
作曲家当然要个性禀赋,否则不可能脱颖而出,当然也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但如果只能偶然写一、两条不错的旋律,那么你的成绩只能如昙花一瞬。要打动更多人,还是要热爱创作,拥有个性化的语言,精湛的技艺,广阔的视野,充沛的感情,这样的话,呈现出的作品才能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直指人心。所以我觉得一个作曲家想要成功,需要集五个方面于一体。
从您担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以来,音乐学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请您就管理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大家进行分享。
杨青:我觉得首先是要设定办学目标。当院长和作曲家其实并不矛盾,作曲家要调动很多的音符来达成创作的艺术价值,每一个作曲家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就能大致判读出最终呈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质。院长和作曲家一样,首先要清楚学院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并通过调动所有的师资力量来达成这一目标。简单来说,就是能把所有人都团结到一起,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奉献精神和劳动,这样
在国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了影响力,也一定要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所以我们也在积极
我们学院也在与美国肯恩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德国汉堡音乐学院进行艺术交流,建立了紧密、深层次的学术合作。我们学院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请他们的演奏家进行演奏,他们的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请我们的演奏家进行演奏,双方学校共同组成演出团队,演出各自作曲家的作品,这种深度的学术合作开拓的比较好。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不仅要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上也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的这种交流会持续开展。这种深度合作,也让我们的教师看到,中国的艺术教育和国外存在哪些差距,国外院校教师的艺术状态是怎样的,我们能不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状态。
之后,全国又搞了一次比赛,是由文化部主办的“文华奖”,其中也有民间组合的比赛,我们这个团队仍然选取“江南丝竹”的作品参赛,我们获得了最高奖项。作为评委之一的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对某一个乐团说道,你们真应该向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习,他们这个团队基本都是北方人,但是他们对于“江南丝竹”的深刻理解和体会超越了很多人,他们确确实实热爱“江南丝竹”。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让我们的教师感受到很多民间的艺术都是瑰宝,这些民间艺术应该进入我们的课堂;第二,之前大家都是单打独斗,比较零散,很少在一起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大家能在一起互相切磋,探讨音乐、精诚合作,促进了教师们对于音乐的深层领悟。
这个团队不仅演奏民间乐种,他们还与韩国和美国同行们合作演奏现代音乐作品,这个团队现在彼此之间非常默契,大家对音乐的追求,对艺术的追求,慢慢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都有着更高的追求。
我觉得办学的意义在于,第一、要选定一个目标,确定你想做成什么品质的音乐学院;第二,要有自己的艺术品牌,不管是舞剧也好,演出团队也好,要让社会上的其他院校能够信服,不能只是自吹自擂,要有实实在在的艺术品牌,这样别人才能对你真正服气。
我来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当了十几年的院长,我们的教师非常的配合,十分支持我的工作,我们的教师也很优秀,大家能够在共同追求相同艺术目标的情况下,逐渐融合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虽然当中也有矛盾,也有对于艺术的不同见解,但是在艺术的总体走向上大家都是一致的、团结的,这也是我当了十几年院长的慰藉所在。
请您介绍一下您作曲的风格和特点?
杨青:其实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我既写过民乐,写过独奏、室内乐、合奏协奏曲,不同类别从小到大都写过,我也写过交响乐,写过独奏室内乐,包括大型的乐队。我还写了五、六部舞剧,第一部舞剧《兰花花》是民乐,剩下的四、五部都是用交响乐创作的。我创作了很多影视音乐作品,和吴子牛导演,张今标导演都有过合作,比如《国歌》、《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磨坊》等作品。
我觉得每一个作品的风格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的作品委婉细腻,有的作品比较抽象,每个作品呈现出的感觉都不尽相同。
有些人说我的风格带有一定的文人特色。我作品中的很多题目都和竹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雨竹》、《竹影》、《竹语》等。竹的挺拔洒脱、正直清高、清秀俊逸是我国文人的人格追求,这也可能是我钟爱于它的原因之一。
我很喜欢传统的古琴曲,经常会去欣赏。我非常欣赏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特质,气节以及对艺术的追求,虽然他们的追求截然不同,但总体来说,他们都具有文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会直接反应在他的作品当中。他们大多数都忧国忧民,对大地有着深深的热爱。很多人都听到过古琴名曲《高山流水》,知晓音乐背后的这个故事。俞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并描绘到“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在钟子期去世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这种交往反映的正是创作者和欣赏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感人。
总的来说,我很喜欢从中国古代到中国近代的大知识分子,我特别欣赏他们的气质、气节、审美以及他们对于美的追求,还有他们对于民族的责任感,甚至抱负。我努力的想在我的作品中展现出这样的气质。
-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