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音抒画 —— 我“看”到的秦文琛
邵琦文 / 作者
作家余华在《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写到:“……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1]这段话使笔者想到秦文琛专场作品音乐会[2]节目册中,对乐曲《听谷》的介绍:“多年来,我用了大量时间在研习中国画,对宋元山水画尤其喜爱。这些山水画直面大自然,并理性地表达出了自然的精神。《听谷》受到了宋元山水画意境的启发,试图通过音响空间和色彩的变化,表达出对大自然声音的想象。”笔者不禁感叹,这是一位“绘画影响了他的音乐”的作曲家!

谈起绘画,起初只是秦文琛大学毕业后的一个业余爱好,闲来动笔画几张,笑称自己“等到什么时候作曲做不下去,就转行当画家”。当他发现这个爱好开始对自己的音乐创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时,中国画中的神韵已然流淌在他的音乐中了。[3]
访谈中秦文琛问道,“你怎么看《太阳的影子》这个题目的意思?”太阳为什么会有影子呢?笔者回答:“是阳光照射下,云彩和草丛的影子吗?”只见他弯起眼睛,笑着说:“你这个当然也是一种太阳的影子。可你知道吗?内蒙古的繁荣是最近15年的事,我小时候没有手表可以戴。放牧的时候,为了知道时间,我会用一根木棍插在草地上。无边无际的草原像是巨大的表盘,太阳的影子就像是悄无声息的指针,丈量着光阴的身影。”笔者在惊讶之余追问,《太阳的影子》是一部从一到十的系列作品,它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或寓意吗?秦文琛说:“不,写成系列就是在不断地重复,讲同一个故事——童年时在草原上的记忆,青草、云朵、风和空间。”
对大自然的挚爱使秦文琛获得音乐创作的原初情感力量。“这种情感的力量就像是海底的暗流一样,而技巧、思想和信仰等等,都是海面的波涛,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来决定的。[4]”秦文琛音乐中所描绘的客观对象、标题内容、旋律结构等都与自然有关。他说:“我很重视自然,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艺术,人类只不过是模仿自然而已。”这样的艺术思想贯穿了他音乐创作的各个环节,其中蕴含着一种庄子式的、心灵—自然的哲学意味。在有相似意趣的中国古代山水画中,他看到了符合内心期待的,音乐发展的终极答案。中国山水画不仅可表现大自然的客观现实,还可表现画者对待现实空间的态度和意识、对自然与人文历史的认同感、地域归属感及个体的生命体验。[5]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6],秦文琛的音乐中透露着山水画般的自然亲近,没有类似西方艺术中对自然的掌控和征服感。不论其音乐内容是一时之景还是具体的事物或空间,它都不是个别的、局限的,而是广阔的、充满整体山光水色气韵的。音乐本体材料形式具有特殊性,其艺术展现与表达的实现由不同音高的音符运动组成。秦文琛认为音乐的这种高度抽象美如同山水画中的骨法、线条、呼吸、气韵、构图……中国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自然中的形象和场景,更在于构成画面的线条和色彩,亦即笔墨本身。笔墨和音乐都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的相对独立的美。秉承着这样的音乐美学观念,秦文琛音乐中的自然,清远又不失温暖,是本色的人的自然。

一、音画—自然的连接
秦文琛的音乐中有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宽广性和空间感。这种空间感充斥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且不受乐曲篇幅和编配形制的影响。独奏作品《琵琶辞》没有单薄感,乐队作品《云川》没有逼仄感。“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7]由画面气韵使观者有如身临其境,这是北宋的山水画,也是秦文琛的音乐。全然、整体性地描绘自然的同时,听者的审美感受在宽泛的、不确定的旋律空间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大地·云影》中营造出青黑色的基调,12件阮震奏和音,不同声部错落叠置,构成云影音画的明暗对比与留白。云朵在空中聚集又消散,光束在风沙中交替摇曳,模糊了时光的界线。微分音于纷繁中营造出空间的清冷迷蒙与阔远无边,同时又因其架构于明晰舒展的旋律线条中,随着时间的展开,这一特性音色晕染出思绪徜徉的边际。
北宋山水画的客观性整体描绘特质,使得它可以展现地域性自然景观的差别。秦文琛音乐中的“宽广性和空间感”,也是一种地域性的音乐特征。和《太阳的影子》一样,《大地·云影》中展现的云,不会在桂林清幽回转的山水上空出现,不会在上海鳞次栉比的大楼上空出现,它只属于鄂尔多斯草原那样宽广纯净的天地中。此外,秦文琛没有局限于地域性的框定,而是将这种地域性特征内化为一种广阔的音乐气质。对比同受宽阔平原环境影响的拉赫马尼诺夫,“老拉”的宽广是带着寒气的灰冷色调,秦文琛的宽广则是于明暗掩映之中浸渍着的厚重的温色调。


二、音画—线的艺术
秦文琛的音乐空间中,旋律流动是自然、完整、顺畅的。他认为,声音遵循自身的逻辑关系,就像一个球弹落到地上,会经过多次回弹、滚动直到停止。好的音乐同样也有自己的运动过程。一次讲座中,秦文琛曾这样介绍《云川》:“这首曲子使用了音响展开的写法,它更像一幅山水画,遵循着声音自身的逻辑关系,趋向自然,就像黄河九曲的自然流向,茫茫草原一望无际的延伸,阴山山脉的连绵不断。”[8]
笔者认为秦文琛所强调的音乐“逻辑关系”不仅是指声音科学的物理规律,还包括对中国古典艺术中,哲学和美学的追求与掌握。如果观察自然是获知事物的物理规律并由此生发出音乐灵感,聆听传统音乐是对音乐素材的积累,那么研习中国山水画就是一种学习中国艺术审美和精神内涵的方式。这种方式帮助秦文琛将心中的自然大美以诗意的,高级的方式表达出来。
秦文琛的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息,技术的痕迹在音乐中被巧妙隐匿。乐曲《艳阳九月》中,表面上的九月仍是一副青山绿水的样子,但乐句的深深浅浅,高高低低,昭示了再浓烈的艳阳也无法阻挡的生命轮回的趋向。早晚弥漫出的寒意正偷偷地将生命的绿意抽离。乐句间的空拍创造了余音回旋坠落的间隙,这成就了全曲一种惰性的味道,艳阳下九月的味道。
这正是南宋山水画的诗意——虚实相生,计白当黑,无画处均成妙境。每一乐句,或浓或淡,或急或疏。笔墨入水,拨
每创作一部新的作品,秦文琛一定会自己上手在乐器上找感觉。如果这件乐器之前没有接触过,他会直接买来自己学。同样的,为了对画作上的笔墨铺陈、运笔的力道和效果、意境的勾勒与呈现等方面有更深切的体会,秦文琛积极地研究和练习绘画。这是一种“庖丁解牛”的精神。“任何技艺,包括文艺,达到这种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熟练统一,便是美的创造。”[9]如果说目的性是视觉或听觉艺术的呈现结果,那么规律性将极大地决定着目的性结果的完成度和质量。很多趣味的东西,只有实践体验过它的创作过程,才可以看到它,进而运用到下一步的创作产出中。大量民间民族音乐的听觉积累和个人的生活体验,造就了目的性的感性认知。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理想和风格,具体到一部作品的内容和呈现形式,则是新的目的性结果的创作。这一新的目的性创作需要认知呈现方式的本体并娴熟掌握技术表达。除乐器自身的形制、音色、音域等参数性知识外,具体的演奏技法和音响效果也都属于乐器自身的语言系统,这便是如牛骨经络一般的规律性。秦文琛的音乐总是“美的创造”——娴熟地合“乐器自身的语言”与“独具一格的目的性结果”为一体。
秦文琛曾在多次访谈中谈到:“我看过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小孩画画,他们凭直觉画的画都是富有美感的,比例和色彩都很到位。反而许多经过严格技术集训的高考美术生,他们画出的画是了无生气的。音乐创作也一样,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直觉上去。”笔者认为,这种创作直觉的抒发需要两个要素:直觉积累和干扰排除。
古代书画家黄公望为能在笔墨中同构自然的气势和生命的力量,常独自一人坐在风雨中。秦文琛儿时在草原的生活,也为他之后的音乐创作积淀了无意识的倾发。在他的记忆里,儿时的画面总是那方辽阔的土地。忽大忽小的气流、或明或暗的光线、看不厌倦的云朵、记不清数了多少遍的牛羊……这种深切的自然体验加之他对生活、艺术、人生的思考以及艺术精神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音乐创作。他对自然与音乐的理解和表达,像树一般扎根在深厚的土壤里,勇敢地朝向无尽的高空伸展,探寻艺术与爱的真谛。
此外秦文琛每完成一部作品都会通过写毛笔字、画水墨画等方式对它们进行“告别”,像是电脑定期清理硬盘一样。对于作品风格的界定、技法是否足够“有品头”之类,他一概不考虑,一切都围绕着音响设计。有意识地排除内外干扰,才能达到“作者亦不自然所以然”的成果。有同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秦文琛“舍弃了社会和人事,集中注意在人的生命与宇宙自然的同构呼应,从而才注意和突出了由全身心与自然规律长期呼应而积累下来的,可以倾泻而出的无意识现象。”[10]

《群雁-向远方》中,全曲只用了八分音符一种节奏型,这使乐曲具有整齐划一的点状笔触特征。两件中阮同时围绕着单音D进行不急不缓、或高或低的八度扩展和同度叠置。泛音在同一声部的音与音之间,乐句与乐句之间,两个声部之间,形成了“虚”与“实”的交错。随着四四拍的节奏律动,偶尔变化的音高像是群雁排成整齐的人字队形,在高空中进行黑色的点线变换移动。音符和节奏编织成的这种净化的,“有意味的形式”,令笔者想到远古时期的华夏民族在各种陶器上刻画的几何花纹。这些花纹原先是完全写实地模仿一些动物形象,后来逐渐向写意的方向演化,保留最具象征性的线条,发展成为一些点、线构成的几何图形。秦文琛音乐中的旋律线条,脱离了具体的事物图景,却又再现了宇宙运动的规律和力量。线条自身的形态,一如墨色自身的浓淡、位置,它们所传达出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和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
“线性音乐就是简单音乐”的思想,是只能看到画面线条形态的思想。而秦文琛看到的,是每个线条为传达出共同的意蕴主题所呈现的形态。他品味着线性音乐的灵魂,并在创作中传达出线性音乐真正的品格。中国古人喜欢用人的自然生命因素来阐释文艺。“骨法形体”“筋血肌肉”“畅神”“游仙”等,它们既与人的生理、身体状貌、先天气质相关,又超脱了具体的有限感性存在,追求与整个宇宙天地的沟通交流。“线”就是对筋骨神韵的提炼和勾勒,它不仅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的相对独立的美,还可传达出人的种种主观精神境界、气韵和兴味。所以看似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中国音乐完全是一种“感觉”的艺术。娴熟地掌握必要的音乐技术之外,还要有深厚的人文修养、丰富的审美积累和个人风格的塑造,才有可能真正驾驭好这一“线性艺术”。

乐曲《五个人的合奏》中包含了中国“最简单”和“最复杂”的音乐——五件乐器共奏一条单旋律,秦文琛只改变了其中一类乐器的定弦,旋律进行中就会不断地出现微分音。这个思路貌似简单,然而它是没有听过蒙古族赞歌、地方戏曲二人台、西南多声部合唱、潮州音乐“一音三韵”的西方作曲家所不能想象的。这样的微分音效果不能像里盖提的微分音技术一样被公式化地表达。“宽线条”的音乐进行是富有灵魂气息的旋律。这种微分音的处理方式抛却对音响运动的机械推导,以“不确切的准确”方式,在还原作曲家内心对民间音乐记忆的同时,也丰富了微分音音响效果的表现空间。秦文琛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学习了用现代作曲技术的视角分析古典音乐作品。从中他发现古典与现代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经历使他谙熟于通过现代视角将传统音乐中已有的音响效果加以提炼和处理,在突出传统音乐形式特征的同时,阐释了个人对传统和现代间关系的见解,使中国传统音乐焕发出新的活力。
英国当代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曾赞叹于卷轴画《康熙南巡图》[11]中散点透视法的运用。霍克尼深受画中所营造的视觉丰富性和时间层次感的启发,颠覆西方传统焦点透视法,创造出充分展现自己时空观的视觉语言。对比秦文琛与霍克尼,二者虽都是以现代眼光去看待中国传统艺术并受其启发,但二者传承和发展的是各自民族的艺术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这使他们的艺术作品带有截然不同的本土气质。
近代以来,当西方艺术家们不断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看待中国艺术中的形式美学与哲学思辨时,一些中国艺术工作者,特别是音乐领域,出现了“线性音乐是简单音乐”的论断,并一味地追捧西方复音音乐的“丰富表现力”。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广泛地学习和容纳各民族音乐文化,是发展本民族音乐的方法之一。但只有将本民族的艺术精髓掌握透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的,有历史意义的真正进步。田青老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发文表示,“中国传统音乐中古老的‘线性思维’应该像一条巨龙,腾飞在更广阔、更深邃的空间里。中国画家们做到的事,中国的音乐家们,也应该做到。”[12]显然,秦文琛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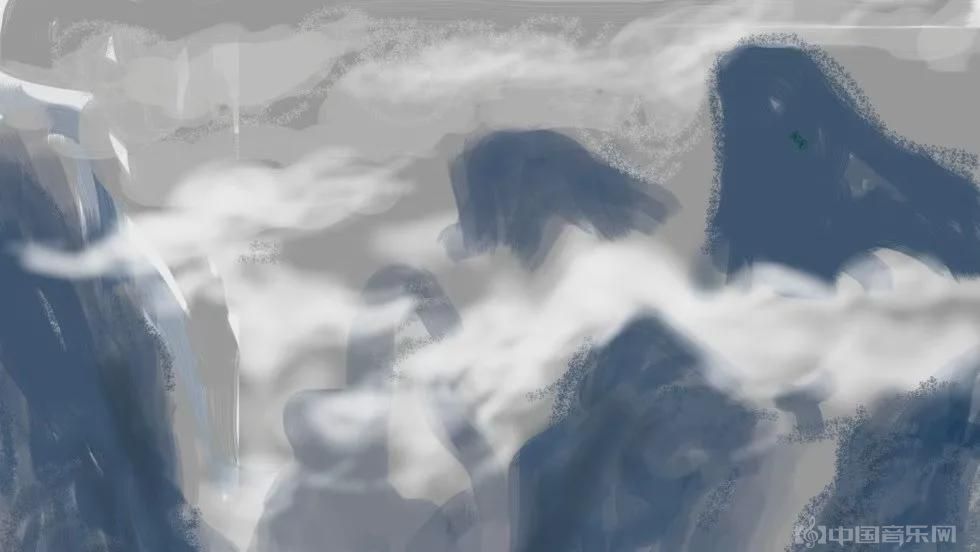
三、音画—审美与情感
宋代山水画中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无我之境”。情感藏在画面的深处,画家通过作画,间接地传达出对乡村景物山水牧歌式的,美的理想和情感。开福森曾说:“在万物生命中,艺术家努力追求的是自己的灵魂。也许更准确地说,是艺术家努力在绘制山水时投入自己的灵魂与生命。”[13]秦文琛的音乐同山水画一般,基于人对于天地力量的从属地位,精神上摆脱了物欲的负重而向内醉心于沉思。在那流动着的广阔而真挚的音响中,传递了永恒的天地之道。人不过是造物的很小一部分,是暂时的,易逝的。这种微妙的精神也洋溢在每一幅高贵的山水画中。秦文琛的音乐需要像欣赏山水画一样安静下来,细细品味。情感表达可以含蓄,也可以赤裸裸。相较于情感奔放外显的浪漫派,他更欣赏和向往巴赫的赋格音乐、埃及的绘画和罗丹的雕塑等这类情感内敛的艺术。他们高级、节制而永恒。秦文琛的音乐虽形同山水画中的“无我之境”,但其精神实质则更具有深刻的超我精神。
《燃烧的云》相较秦文琛的其他器乐作品,具有明显的歌唱性,是秦文琛目前为止创作的最为直接抒情的作品。数件阮同音轮奏,以声部间的错落铺陈实现了乐音的延展,拉长了同一音的时值。高声部在歌唱的同时,低声部以连绵的持续音相衬。整曲含蓄而朴素地表达了火烧云带给作曲家的心灵震撼。其中的情感既不是动物式的自然感性,也不是先验的产物或神的恩宠。超越而又不脱离感性,这是一种具有积淀本体的感性情感。[14]

《向远方》音乐会海报的封面也可见秦文琛的音乐审美理想。这幅名为《光》的画,出自秦文琛的同乡好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朝戈。画中的蒙古人用双手遮挡着眼前的阳光,望向远方。虽是油画,但青灰的色彩倾向与富于感官性的西方近现代油画风格大不相同。画面充斥着古典壁画沉稳与内敛的气息,将三维空间加以压缩、平面性地推延,使得复杂微妙的色彩从局部扩展至整体。朝戈没有强调瞬间的辉煌和经验的断片,而是在直觉的基调下,试图恢复人类历史上某些永恒的价值。[15]当下,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都不断地有一些极端化的表达,但时间和历史将会对艺术的走向进行修正。[16]朝戈在绘画中放弃油画成熟期的语汇,回归早期绘画的质朴,这与秦文琛的音乐理想不谋而合——在保有历史与传统精华的同时兼具凝练的现代性。秦文琛的音乐中没有传统的或西方的界限,没有新,也没有旧。尽管他的音乐中有雅致的意蕴之美,可你就是不能界定他的音乐。因为他只用那些技术和经验来表达忠于他自己的、最真实的声音。在音乐中追求永恒,在审美中追求“逸品”,他的音乐具有完整的个人品格。他们的作品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
我想秦文琛也许有和作家余华相近的感受:“绘画开始影响我的音乐创作了,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绘画的神韵,我开始思考陆探微的永恒之境和米芾的线条,在他们的画作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大自然的美学和哲思,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从魏晋到宋元……“


[1]《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余华,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
[2] 2019年10月11日19:30,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厅举行《向远方——秦文琛民乐作品音乐会》。
[3] 笔者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采访了作曲家秦文琛。
[4]《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余华,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
[5] 《山水画创作中的“地方”聚焦》耿杉,《美术》2019年05期。
[6] 中国美学史上“师造化”理论的代表性言论,由唐代画家张璪提出。意为: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但是自然的美并不能够自动地成为艺术的美,对于这一转化过程,艺术家内心的情思和构设是不可或缺的。
[7] 宋代郭熙著,《林泉高致》山水训。
[8] 《坚守·突破——“秦文琛近期三部管弦乐作品创作”讲座随记》张宝华,《音乐生活》2019年05期。
[9] 《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
[10] 同6.
[11] 《康熙南巡图》是以康熙皇帝南巡为题材的大型历史图卷,共十二卷,总长213米。展现了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时,从京师离开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
[12] 《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田青,《中国音乐学》1986年04期。
[13] 《远山的呼唤——朝戈》殷双喜,中国美术家网。
[14] 同6.
[15] 《远山的呼唤——朝戈》殷双喜,中国美术家网。
[16]《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田青,《中国音乐学》1986年04期。
参考文献
1.《美的历程》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
2.《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6月。
3.《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余华,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
4.《福开森与中国古代绘画研究》赵成清,《美术》2019年08期。
5.《坚守·突破——“秦文琛近期三部管弦乐作品创作”讲座随记》张宝华,《音乐生活》2019年05期。
6.《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周勤如,郭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02期。
7.《向远方——寻找自己的声音》沈云芳,《人民音乐》2013年01期。
8.《远山的呼唤——朝戈》殷双喜,中国美术家网。
9.《山水画创作中的“地方”聚焦》耿杉,《美术》2019年05期。
10.《秦文琛〈向远方〉(上)持续型
11.《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田青,《中国音乐学》1986年04期。
12.本文以《向远方-为中国乐器而作的30首室内乐曲集》(2010/11)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原载于《音乐文化研究》2020年第四期,并获得第八届“上音院社杯”音乐评论“学会奖”一等奖。
邵琦文:中央音乐学院2016级音乐学系本科学生,师从王次炤教授。她的学术论文在《人民音乐》和《音乐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
-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